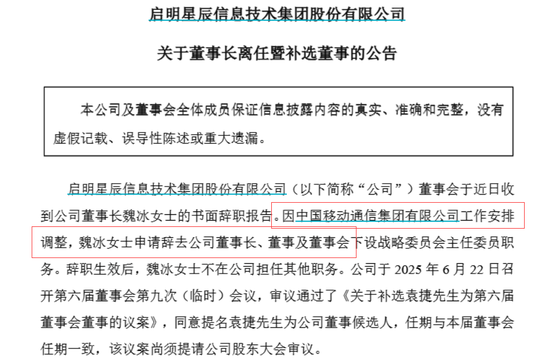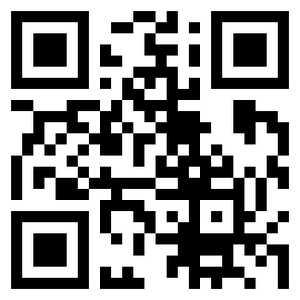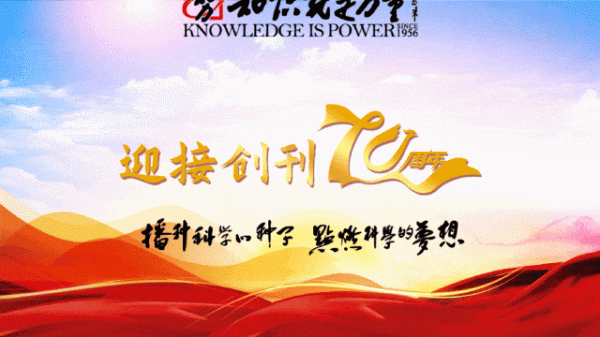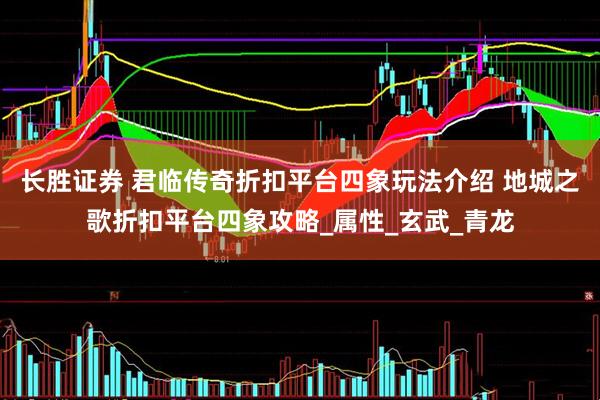黄河几字弯道的西北角,鄂尔多斯如一颗被沙漠包裹的明珠御龙优配,夹在毛乌素与库布其沙漠之间。
这片8.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约为五个北京大小,21世纪初期总人口仅130万,地广人稀且曾是毫不知名的三线草原城市。
但鲜为人知的是,其戈壁之下蕴藏着全国约六分之一的煤炭,这得天独厚的资源,让它在改革开放后以惊人的速度崛起。
2010年,鄂尔多斯GDP总量从2001年的171.1亿元飙升至2643亿元,人均GDP高达17万元,是当时上海的2倍,甚至可与香港比肩,一跃成为中国首富城市。
一年后,住建部联合高禾投资发布的报告显示,这里资产过亿的富豪超7000人,上千万资产者至少10万,意味着每217人中就有一位亿万富翁,每15人中就有一位千万富翁。
展开剩余91%人们曾评价鄂尔多斯是能频繁验证“贫穷限制想象力”的城市,牧民开着路虎放羊的“报复性消费”生活却仅持续不到10年。荒野上拔地而起的万丈楼台,最终迎来了空无一人的街道,摩天大楼与雕像在寂静中矗立,形成豪奢与荒凉的强烈撕裂感,“草原迪拜”的美誉也随之变成了“鬼城”的标签。专家学者以它为隐喻,抨击中国疯狂城市化进程中的种种问题,在这里,投机与债务、繁荣与衰退的转换不过转瞬之间。
20世纪80年代,若问内蒙古当地人最穷的地方在哪,答案多是伊克昭盟——鄂尔多斯的旧称。
这里以农牧业为主,气候极度干旱,常年受风沙侵扰,土地盐碱化严重,广种薄收是常态。
曾有牧民为买一盒火柴,需在沙地里跋涉十几公里;村里政府送来的12英寸黑白电视,也常因风力发电机不给力而中断播放。当地老人们打趣说,走西口停在鄂尔多斯的人,都是没力气北渡黄河才留下的,“全家住一间土坯房,两代人同睡一排炕、一条被子”的顺口溜,道出了当时的窘迫。
然而,上天似乎以另一种方式补偿了这片贫瘠土地。
20世纪50年代,一支牧场勘察队在鄂尔多斯高原发现了阿尔巴斯白山羊,其羊绒直径普遍低于14.5微米,洁白柔软、纤维长、光泽好、净绒率高,堪称山羊绒中的佼佼者,被列为全国20个优良品种之一。传说意大利人曾偷偷运走几只,想引入本国,可这些羊离开故土后水土不服,最终无一存活,外国商客只能无奈接受从伊蒙进口羊绒的事实,伊蒙人由此站在了离财富最近的地方。
1969年,伊克昭盟东胜区建立起中国最早加工山羊绒的伊盟绒毛厂。
1979年,该厂得知日本设备能从1200吨原绒中提取500吨无毛绒,比国产设备多近200吨。尽管日本三井株式会社提出的2300万元引进费用远超当时全盟1600万元的年财政收入,但伊盟领导仍以贸易补偿方式引入全套设备和技术,用生产的产品冲抵价款。这一年,伊盟羊绒衫厂作为内蒙古自治区改革开放后的首个招商引资项目落户东胜,成为当地致富之路的起点。
1984年,时任厂长王林祥赴日考察,发现日本百货店中来自伊盟的羊绒衫挂标后售价暴涨十几倍甚至几十倍,遂意识到创立本土品牌的重要性。回国后,他打造了极具民族与地域特色的“鄂尔多斯”品牌。1989年10月,“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的广告登陆央视黄金时段,在上海平均月工资仅217元的年代,企业斥资37万连续投放半年广告,鄂尔多斯借此成为最早发掘央视流量红利的企业之一,迅速闻名全国。
1991年,北京、上海、深圳等八大城市均设立了鄂尔多斯经销部进行直销。
但羊绒生意的隐忧很快显现。山羊对草牧场破坏极大,1998年至2000年,伊蒙沙化退化的草原面积占可用草原面积的80%。
2000年春天御龙优配,一场罕见沙尘暴席卷北京,不少人将矛头指向伊蒙的山羊,伊蒙不得不采取东部四季圈养、西部4月1日至10月1日圈养的政策,山羊数量减少导致羊绒产量受限,行业天花板渐显。此外,羊绒仅用于冬季服装,消费人群有限,且1998年金融危机后,欧美、日本和东南亚等主要消费市场低迷,羊绒销量受阻,伊蒙不得不另寻出路。
这条新出路的伏笔早在80年代就已埋下。
1982年春天,陕西省一八五煤田地质勘探队奉命开赴陕北榆林,半年后提交的报告显示当地发现780亿吨大煤田,毗邻的伊蒙由此引起国家煤炭部关注,成为新的探测目标。1986年,内蒙古自治区煤田地质勘探公司10017勘探队提交的报告证实,伊盟地下蕴藏丰富煤炭资源。
后来证实,伊蒙在全国最大煤炭富集区占据核心位置,8万多平方公里土地上,七成以上地层有煤炭,探明储量2102亿吨,约占全国六分之一、内蒙古二分之一,与陕西榆林、山西朔州共同构成中国煤炭金三角。
消息传开后,央企神华集团率先进入,占据优质煤炭资源,留下不菲税收。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央提出“有水快流,大中小并举”的发展策略,伊盟盟委书记表示要让民营企业“做正席、唱主角”,民营煤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但因交通闭塞、距工业中心远,且山西牢牢把控能源市场,当时的伊盟仍难与邻近的大同相比。
2001年,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报请国务院撤盟设市,“鄂尔多斯”取代“伊克昭盟”,这个在蒙语中意为“众多宫殿”的名字,也带来了新的时代机遇。21世纪初期,中国电力、建材、钢铁、化工等重工业勃兴,对煤炭需求激增,而山西部分地区煤炭储量逼近枯竭,产量和效率难以满足需求。加之西部大开发战略推进,靠近山西的鄂尔多斯凭借地理优势,迅速填补市场空缺。
2003年成为煤炭行业黄金十年的开端,如飓风般席卷沙丘,裹挟着鄂尔多斯的命运驶入致富快车道。这一年,鄂尔多斯原煤总产量达8103万吨,首次超过长期居首的大同,跃居全国第四。次年,本地煤炭坑口价从20元左右涨至40元,大量南方人前来收购煤矿,北部普通煤矿售价几百万元,南部经济区煤矿可达2000万元。多数鄂尔多斯人对突如其来的财富毫无准备,纷纷出售煤矿,用他们的话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就发财了”。
2005年初,煤炭局计划将每吨100元作为当年奋斗目标,可实际煤价大幅上涨,最高超600元/吨,煤矿投机炒卖之风盛行。有煤老板以40万元买下煤矿,搁置两年后卖8000多万元,一年后该煤矿又以10亿元成交,十几天换一次矿主成常态,速度之快令人咋舌。
地方政府察觉到小矿井的生产能力和安全问题,以及失控的煤矿投机,启动三年攻坚战,对产能小、地块邻近的煤矿整合重组。仅一年多时间,552座煤矿关闭50%,仅剩276座,至2007年底全部实现正规化、机械化开采。整合后,煤炭为鄂尔多斯经济注入强劲动力,2005年煤炭产量1.17亿吨,2009年达3.3亿吨,四年间产量增长近2倍,价格增长7到8倍。彼时,无论国企还是小煤矿,运煤车都在矿门口排起长队,人们争相交钱以优先装运。
除煤炭外,鄂尔多斯还有粘土、高岭土等资源,天然气储量约占全国三分之一,“煤炭、稀土、天然气、羊毛”被简称为“扬眉吐气”,让鄂尔多斯人真正扬眉吐气。矿区常见老板们背着整袋钞票存款,井下工人月薪8000至1万元,井上工人4000至5000元,就连捡煤块的农牧民一晚上也能收入不菲。
征地补偿中,地方政府常按国家最高标准甚至超标准执行,每户农牧民动辄五六百亩甚至上千亩的土地和草场,让“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为现实,因拆迁与征地身价百万、千万者比比皆是。
2009年,第八届中国企业领袖年会上,内蒙古自治区副主席宣布鄂尔多斯人均GDP将超越香港。当时,鄂尔多斯生产总值达2100亿元,人均GDP13.4万元,达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虽距香港的20.5万元仍有差距,但这个塞北小城与东方之珠在经济版图塔尖的相遇,仍令人惊叹。一位外来商人用“变态富”形容这里,类比“变态辣”,凸显其财富的极致程度。
财富积累后,如何驾驭成为政府与煤老板的共同课题。鄂尔多斯市政府所在地东胜城区仅有三横三纵路网,煤矿产业发展带来大量外来人口和农牧区转移人口,巨量财税收入支撑起新区建设,康巴什新区随之动工。新加坡规划团队设计的方案中,城市中心是成吉思汗广场,以“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为主题,政府斥资上亿元开凿运河,建成当时亚洲最大景观喷泉。
交通瓶颈也随之破解。2007年鄂尔多斯机场建成,初期航班乘客寥寥,有时甚至少于乘务员,可随着财富集聚,机票时常售空且从不打折,短短两年多后,航站楼不堪重负,政府随即启动第二座航站楼建设。
普通民众则将激情投入高奢消费,高档酒楼以高价“赌翅”为标配,食客口味挑剔,酒店频繁更换总厨,甚至有酒店与香港餐饮集团合作,请香港师傅料理鲍鱼,餐饮负责人被挖角时,年薪达50万元外加一辆奥迪车。街头常见人们闲聊“昨天请朋友吃鲍鱼才花几万块”,相比美食,老板们更热衷豪车。
2010年9月30日,首届鄂尔多斯国际车展上,3800万元的布加迪全新敞篷跑车展出不到1小时即被预定,当天总销售额超9000万元,1500万元的迈巴赫、两辆兰博基尼、五辆宾利全部售出。传言高峰时期,鄂尔多斯有近5000辆路虎,占中国内地总量的90%,宾利、阿斯顿马丁也于2012年前后入驻,当地人购车如买白菜。购房同样狂热,外地地产商评价其购房需求呈跳跃式增长,斜率陡峭,改善性需求强烈。
有记者目睹,鄂尔多斯太古广场售楼处,一位中年女子打电话称商铺首付1300万,这并非单纯炫富,房地产更是当地人的财富蓄水池。他们买房常整层或整排购入,如同存钱,甚至不愿出租十几套房产,嫌房租少且麻烦。北京华府置业考察发现,2001至2008年,鄂尔多斯人均住房面积达32平方米,合作项目未开盘已获大量咨询预订,甚至有三十多岁客户购买900多平方米房产。
2006年楼市均价约1200元,2009年涨至7000元左右,东胜区2006年前总建筑面积800万平方米,2009年一年就建成1000万平方米,2000至2009年房地产开发规模年均增长39%。
这座160万人的城市,当时有323家房地产开发商,中心区域富丽堂皇的现代高层与独栋别墅,让它宛如“小迪拜”,迪拜酋长“梦想没有极限,唯有持续向前”的名言,成为当地人信奉的信条。
鄂尔多斯民间金融与温州齐名,2010年末银行存款余额1755亿元,贷款1562亿元,存贷比89%,远高于深圳的57.5%和佛山的67.8%,人们更倾向于通过投资公司、担保公司、典当行及地下钱庄进行民间借贷。内蒙古大学调研显示,50%的城镇居民参与放款与借款,月息两分,1万元年收益2400元,远超银行利息。地产开发商和矿主是主要资金需求者,民间借贷手续简便,常为一纸合约甚至口头协议,而银行则需“六证齐全”。
2011年,高和投资与住建部政策研究中心的报告概括其财富链条:煤炭开采产生的巨额财富支撑城市改造,通过征地分配给更多人,再经民间借贷流向房地产和新煤矿,形成循环,仿佛永动机般让众多发达城市黯然失色。
但永动机终究不存在。
2010年,内蒙古煤炭产量首次超过山西,榆林产量仅为鄂尔多斯一半,开始走向衰退,而鄂尔多斯仍沉浸在繁荣中。同年,美国《时代周刊》记者迈克尔・布朗探访康巴什新区,发表《鄂尔多斯,一座现代鬼城》的报道,称这里因房产空置率过高,夜晚漆黑一片,与“天堂”的描述形成反差,将其推上城镇化过速与造城运动的舆论风口。
2012年,鄂尔多斯市长提出产业多元化转型,计划发展汽车装备制造、电子信息、云计算等非煤产业,引入人才,期望三五年内成为新兴工业城市,却因缺乏产业基础难以实现。
这一年,也成了煤炭黄金时代的终点。2011年起,全国煤炭需求停滞甚至萎缩,冶金、水泥等耗煤行业增速放缓,水电因多雨发力挤压火电需求,而煤炭基建投资仍在激增,“十一五”期间达1.29万亿元,2011年4700亿元,2012年5570亿元,鄂尔多斯、榆林、大同间的产量比拼及企业跑马圈地,加剧了供需失衡,再加上环保压力,煤炭行业迎来寒冬。
2012年底,煤炭价格断崖式下跌,一家2011年9月投产、投资12亿元的民营煤企,粉煤价从340元跌至170元,濒临停产。承包煤矿的矿主为回笼资金,即便亏损仍需生产。运煤主干线从拥堵变为冷清,司机们在路边餐馆等待祈祷,煤矿附近餐馆生意惨淡,“煤好一切都好,煤差一切都差”成了共识。
2013年,鄂尔多斯地方财政收入增幅从2011年的48%跌至3%,商品房销售面积2011年降18%,2012年降47%,销售额降49.4%,房价从7000元跌至3700元,高端住宅降价至万元以下仍无人问津。银行门可罗雀,保险公司领导开起小卖部,外来淘金者纷纷逃离,出租车司机盼着合同到期离开,民间借贷老板跑路成常态,道路显示屏播放债务违约者照片,环卫工人清扫着空旷的街道,夜晚的康巴什新区与核心小区漆黑一片,“鬼城”成谶。政府虽计划2013年GDP突破4000亿元、增长11%,财政收入870亿元、增长6%,增加煤炭产量6000万吨,却未能阻止恶化。
2014年,亏损达87.2亿元,财政收入与GDP增速大幅下滑,2015年约70%煤矿停产。
煤商们向政府和银行求助,某企业负责人短信直言,民营企业因互保关系,一家资金链断裂将引发连锁反应,危及上万职工与社会稳定。内蒙古自治区随后出台政策,下调煤炭价格调节基金,减免铁路运费,为煤企减负。德国鲁尔区的转型之路,成了他们的借鉴。
2019年,鄂尔多斯退出30万吨落后煤炭产能,非煤产业增加值增长0.6%,推动煤炭向天然气、化肥、乙醇等深加工转化,规划千亿级工业园区,可再生能源装机容量达313万千瓦,在质朴与迷茫中寻找希望。
这种因过度依赖资源而陷入困境的现象,正是经济学中的“资源诅咒”,荷兰曾因天然气资源经历类似危机。鄂尔多斯十年崛起,三年衰退,在浮华后重归沉寂,散落着致富梦想与劫后余生的感慨。
如今,面对未来发展模式的提问,当地主政者会说:
“依靠资源而不依赖资源”,站在煤炭市场回温的潮头,鄂尔多斯迎来了重新选择的机会。#热点##经济##鄂尔多斯##内蒙古##财经##中国##内蒙古头条##社会百态##民生##爱国#御龙优配
发布于:河南省通弘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